對話渭南|鄉(xiāng)愁上的華州南塬

渭南綜合廣播 | 對話渭南

董卓武,陜西省渭南市華州人。中國詩歌學(xué)會會員,陜西省作家協(xié)會會員,渭南市作家協(xié)會會員。作品先后發(fā)表于《解放軍報(bào)》《中國軍工報(bào)》《前衛(wèi)報(bào)》《陜西日報(bào)》《陜西政協(xié)報(bào)》《西安晚報(bào)》《延河》《詩選刊》《延安文學(xué)》《陜西詩歌》《馮站長之家》等報(bào)刊和網(wǎng)絡(luò)平臺,入選《2016中國網(wǎng)絡(luò)詩歌精選》《長安風(fēng)十人詩選》《長安風(fēng)詩選·中國當(dāng)代詩人卷》等,著有長篇小說《蘊(yùn)空山傳奇》《樓觀》,詩集《董卓武華州詩歌作品選》等。?
華州南塬是一個(gè)寬泛的地理概念,當(dāng)?shù)厝艘话惴Q高塘塬。這里以高塘鎮(zhèn)為中心,周邊有大明、金惠、東陽、圣山四個(gè)鄉(xiāng)鎮(zhèn),我們那時(shí)候叫公社。撤鄉(xiāng)并鎮(zhèn)后,現(xiàn)在只有高塘和大明兩個(gè)鎮(zhèn),管轄整個(gè)塬區(qū)。這一片塬區(qū)過去很偏僻,也很封閉,因?yàn)樗吒呗柫⒃谌A州西南部,從塬下經(jīng)過根本不會想到上面還有一大片溝壑縱橫、臺塬層疊的世外天地。因?yàn)槠Ш头忾],這里形成了獨(dú)有的民風(fēng)民俗,世世代代的塬上人在這里耕種生息,繁衍至今。20世紀(jì)60年代,我在這里出生,又在這里長大。已那年高中畢業(yè)參軍入伍,走出華州南塬。

人是走出了華州南塬,但根還在心還在華州南塬,純樸的南塬培養(yǎng)出來的純潔樸實(shí)的感情還在華州南塬!離開華州南塬以后,我就有了老家、故鄉(xiāng),這是華州南塬以另外一種方式把我和它緊緊相連!在這樣的背景下,我一邊在他鄉(xiāng)行走,一邊回望時(shí)而近時(shí)而遠(yuǎn)、時(shí)而清晰時(shí)而模糊的華州南塬,把它融進(jìn)了我的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之中。
生活艱辛卻如詩
在塬上的生活,做農(nóng)活是很辛苦的。土地承包責(zé)任制以前,孩子們幾乎不參加勞動,除了上學(xué),就是滿天野地玩,那時(shí)候的記憶里全是無憂無慮和快樂。土地分到各家各戶的時(shí)候,我們大都長到十三四歲,正是能幫助家里干活的年紀(jì)。上學(xué)之余,我們就全力參與到家庭的勞作之中。雖然有年少的虎勁,可我還是經(jīng)常被農(nóng)活的累和重干到急眼。這只是一方面,最難受的是那種日復(fù)一日、年復(fù)一年,不知道什么時(shí)候能干完、能干到頭的無望和無奈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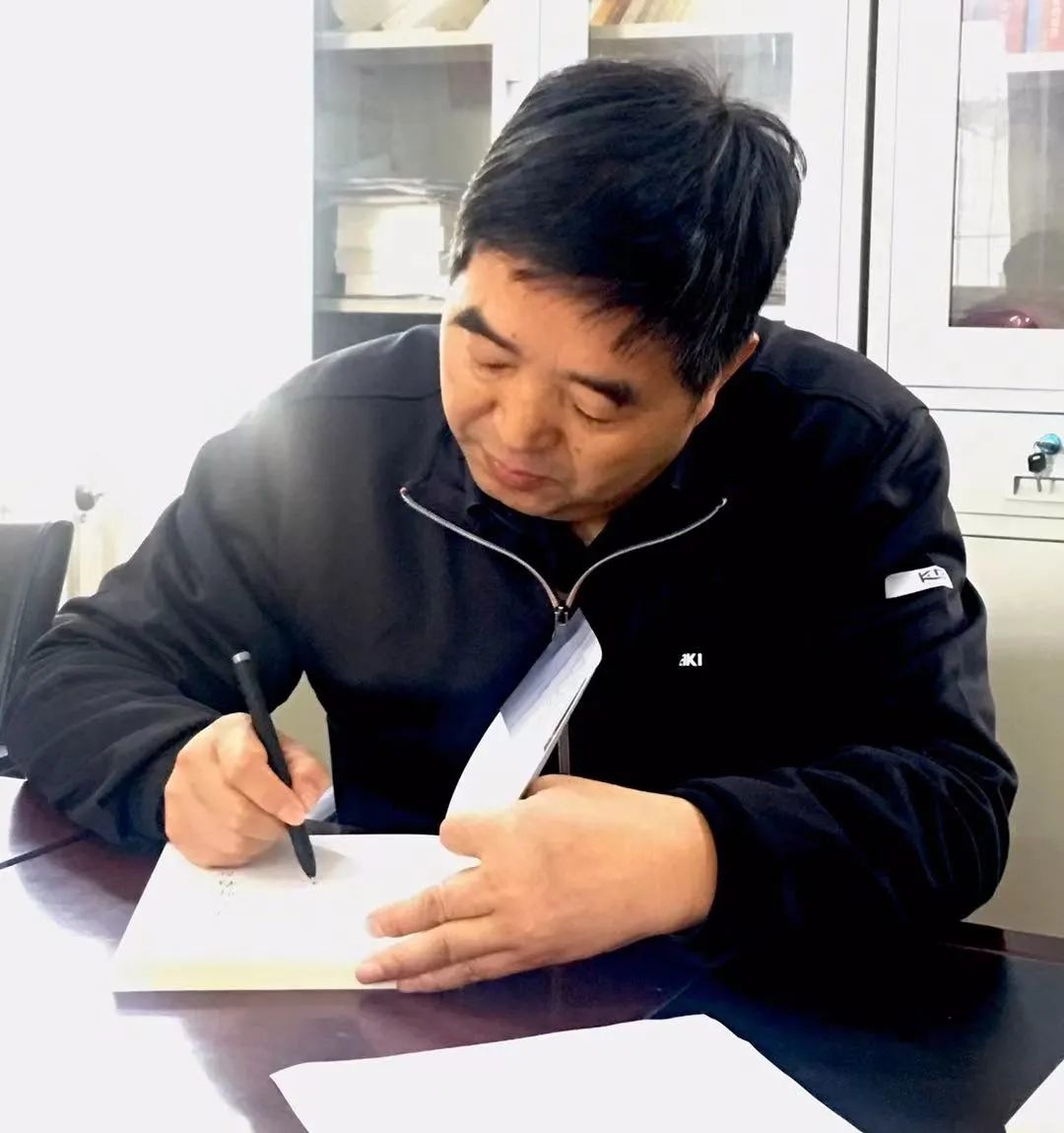
但神奇的事情發(fā)生了,當(dāng)離開了南塬,隔開一段時(shí)間,數(shù)年、數(shù)十年;隔開一段距離,幾百公里、幾千公里,再回望當(dāng)初的南塬,我突然覺得它竟是那么美好、那么純潔、那么難忘,像一首首詩歌一樣,在我心胸里蹦跳。這個(gè)時(shí)期,我寫下了很多關(guān)于南塬,也就是高塘塬的詩歌。如《我的高塘塬》《高塘塬,關(guān)中東部之渭河南岸》《高塘塬上生長莊稼也生長父親》《山水如畫高塘塬》《不忘初心高塘塬》《高塘塬最近也最遠(yuǎn)》《一路回家》《夢想開始的地方——致母校高塘中學(xué)的青春年華》《高塘塬上的光陰》《掛在鄉(xiāng)愁上的柿子》《華州的麥子》《到了部隊(duì),才有了故鄉(xiāng)》等等,從名字上就能感受到濃濃的高塘塬情懷。

在這些詩中,塬上生活的艱辛和苦難不見了,高塘塬成了一片干凈又美好的世外桃源。這不是我的選擇性遺忘,而是因?yàn)槟切┢D辛和勞作在經(jīng)過歲月的沉淀之后,已經(jīng)轉(zhuǎn)換為我精神世界里一抹亮麗的光,照亮了過去,也照亮了現(xiàn)在和將來。曾有一位朋友對我說,他從連霍高速經(jīng)過,看到路上高塘方向的道路標(biāo)示牌,就在心里想起我,想這就是董卓武老師的高塘塬!我聽了挺感動,高塘塬在我的詩中有了生命!

蘊(yùn)空山上有傳奇
歷史上,華州南塬發(fā)生過很多傳奇的故事,蘊(yùn)空山懸棺就是其中一個(gè)。有民間傳說,在明末清初時(shí)期,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禎的四子朱慈烺國破外逃,幾經(jīng)輾轉(zhuǎn),最終來到秦嶺北麓的華州南塬上。朱慈烺在南塬上安頓下來以后,秘密聯(lián)絡(luò)明朝舊部人馬,干下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——反清復(fù)明。朱慈烺雖然占據(jù)高塘塬地勢之利,但隨著清政府統(tǒng)治力量的逐漸強(qiáng)大,復(fù)明的愿望最終卻成為泡影。朱慈烺拋卻心中的國仇家恨,來到蘊(yùn)空山削發(fā)為僧。在他圓寂的那一刻,他終于明白了,世間萬事都不過是一場蘊(yùn)含空意的夢,既無可爭,也無可戀,他遺言讓弟子把自己的尸柩懸空而葬,四周不著泥土,喻義一切蘊(yùn)空。依據(jù)這些傳說故事,從小就在蘊(yùn)空山下生活和長大的我創(chuàng)作出了長篇小說《蘊(yùn)空山傳奇》。2016年12月,《蘊(yùn)空山傳奇》由陜西新華出版?zhèn)髅郊瘓F(tuán)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。
在這篇小說中,我首次用到了華州南塬這個(gè)概念。每個(gè)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一片地域,這里有他深厚的生活根基,有他的感情寄托和精神源泉。華州南塬于我就是這樣。《蘊(yùn)空山傳奇》雖然是講故事,但實(shí)質(zhì)上和我那些關(guān)于塬上的詩歌作品一樣,還是在表達(dá)對華州南塬的那種樸實(shí)樸素的感情,一種從小生于茲長于茲的天然情懷。小說中有兩群相隔三百年的孩子,一群在明末清初時(shí)期,一群在20世紀(jì)80年代,雖然所處環(huán)境、時(shí)代不同,但都有我自己的影子。

我之前的詩歌作品和小說《蘊(yùn)空山傳奇》以及另外一部長篇小說《樓觀》,現(xiàn)在來看,“小我”情懷明顯,過于淺顯直白,表象化的東西多,沒有寫出“靈魂的深”,文學(xué)和藝術(shù)性還不強(qiáng)。當(dāng)然,以我的水平和能力,能不能寫出“靈魂的深”“生命的深”,現(xiàn)在還不敢妄言。但我有一個(gè)目標(biāo),就是要努力寫出“南塬的深”。最近在《延安文學(xué)》上發(fā)表了一個(gè)中篇《家不是老的家》。寫的是在現(xiàn)代化和城鎮(zhèn)化大背景下,南塬和其他廣大農(nóng)村地區(qū)一樣,出現(xiàn)的某種衰敗和凋落。老屋塌了,人進(jìn)城了,莊稼地沒人種了,現(xiàn)實(shí)的南塬和精神的南塬都到了不知道往哪里走的地步。老了的家不再是家,沒有了雞鳴狗叫的煙火,后輩沒有人再想回去住,這是老家的悲哀,也是農(nóng)村發(fā)展的悲哀!在這篇小說里,我表達(dá)了對南塬命運(yùn)的擔(dān)憂和關(guān)注,算是在“南塬的深”上開始了初步的探索。寫作沒有自己熟悉的領(lǐng)地,沒有對過去的深情,就沒有對未來的向往,就會落入空洞、做作和虛情假意。真實(shí)狀態(tài)的寫作,總是從最熟悉的人、事、物開始,從對它們的感受開始,然后再擴(kuò)展到更寬廣的想象之中。所以,我的寫作還要繼續(xù)堅(jiān)持我的“南塬之路”,希望華州南塬能帶給我不竭的靈感和力量!?
編輯:祖鈺
初審:劉瑩
終審:周新宏
編輯:葛祖鈺